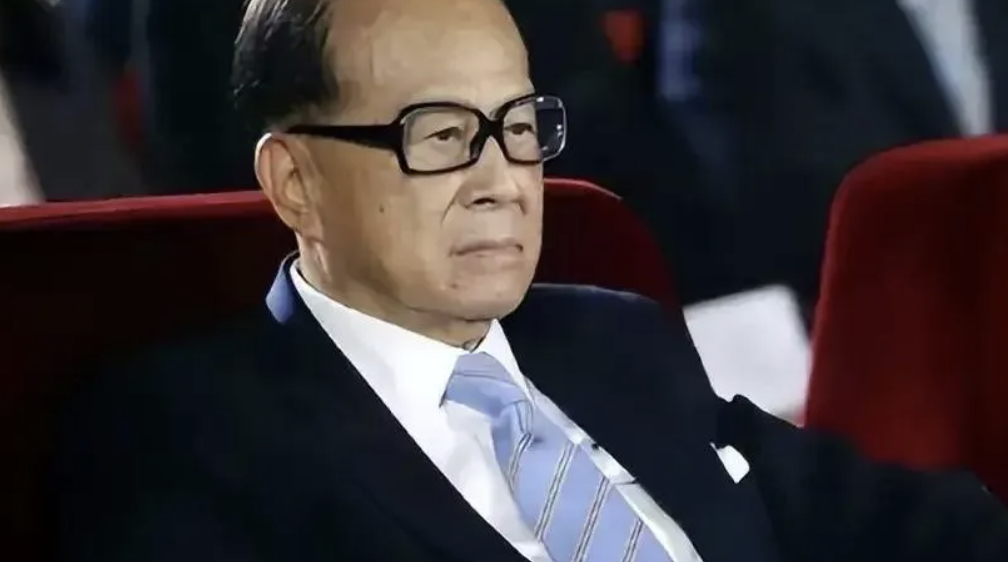“内衣大王”跌落神坛靠卖厂房自救
2025-04-01 |
- 2025-04-01“内衣大王”跌落神坛靠卖厂房自救
- 2025-03-31四大行增发会带来什么影响
- 2025-03-31成交见地量这周能否引发强反弹?散户要有两手准备
- 2025-03-31这些操作让上海“称霸”中国经济
- 2025-03-29估值500亿科技公如今面临破产
- 2025-03-29随着近期市场投资者的四问四答
- 2025-03-28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在中国的活动频繁
- 2025-03-28李嘉诚到底有多少资产?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
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浪潮中,女性生意一度被视为“稳赚不赔”的金矿。
从胶原蛋白到玻尿酸,从医美到内衣,无数掘金者在这片万亿蓝海中起起落落。
而曾经被誉为“中国版维多利亚的秘密”、市值一度高达200亿港元的内衣品牌,却在短短几年内从巅峰跌落,累计亏损超19亿元,市值蒸发近200亿。
如今,这家老牌内衣企业不得不靠出售厂房“美化”财报,试图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喘一口气。
从保安到“内衣大王”
1998年,中专毕业的福建小伙郑耀南怀揣梦想来到深圳,却因学历和资历不足,只能在沃尔玛当保安。
有一次郑耀南偶然路过一家内衣店时,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,10元一件的内衣,竟然在一个小时内销售额达到近千元。
这个发现让郑耀南意识到,内衣或许是门“闷声发大财”的生意。
于是在同年,郑耀南创立了都市丽人,主打“贴身衣物一站式采购”,将内衣、袜子、保暖衣等品类集中销售。
这种新潮的销售方式迅速走红,门店开业即爆满。
而郑耀南的胆识在两次危机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,2003年非典期间,当其他品牌收缩战线时,他逆势扩张门店至50家。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,他又低价收购厂房,夯实供应链,这两次豪赌让都市丽人迎来爆发式增长。
2012年,品牌签下林志玲作为代言人,凭借明星效应迅速打开全国市场。
到2014年港股上市时,都市丽人门店已超7400家,年营收45.53亿元,净利润5.4亿元,郑耀南也以85亿元身家登上胡润富豪榜。
当时的都市丽人,几乎是“线下流量红利”的代名词,粉色门头遍布大街小巷,甚至被戏称为“内衣界的沙县小吃”。
2016年,野心勃勃的郑耀南喊出“万店计划”,门店一度突破8000家,然而,谁也没想到,这场狂奔的终点竟是一场断崖式坠落。
性感神话的崩塌
2018年,都市丽人营收突破50亿元,看似站上巅峰,实则暗藏危机。
此后三年,公司连续巨亏,累计亏损达19.1亿元,股价从2019年初的2.53港元跌至2022年的0.27港元,市值蒸发近200亿。
而且门店数量从巅峰期的8000家锐减至2022年的不足5000家,甚至在2020年关停了90%的门店。
曾经让无数少女心动的“粉色宣言”,沦为消费者口中“老土、质量差”的代名词。
首先,疫情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线下加盟商体系原本是都市丽人的核心渠道,2018年贡献了55%的销售额。
但疫情导致消费力下滑,加盟商库存积压,销售占比骤降至2021年的18.7%。
与此同时,品牌未能及时跟上电商转型,2021年仍有53%的销售额依赖线下零售,而此时蕉内、ubras等新品牌已通过线上营销抢占年轻用户心智。
另外女性消费习惯的巨变彻底颠覆了市场逻辑,都市丽人赖以成名的“快时尚性感”风格,在“悦己经济”浪潮中显得格格不入。
2019年起,消费者对舒适、健康、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激增,而品牌直到2020年才仓促转向“科技、健康、舒适”的定位,错失转型窗口期。
盲目扩张的“万店计划”导致管理失控,产品质量问题频发,再加上一二线城市门店租金高昂,却未能吸引年轻客群。
而创始人郑耀南在2016年后逐渐退居二线,职业经理人的保守策略让品牌在竞争中步步落后。
一场艰难的翻身仗
2021年,郑耀南重掌CEO职位,试图力挽狂澜,他砍掉亏损门店,裁员400人,将战略重心转向租金更低的下沉市场。
这一调整让都市丽人在2022年勉强扭亏为盈,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营收从2021年的33.6亿元降至2023年的27.57亿元,同比下滑8.4%。
更尴尬的是,2024年上半年净利润飙升215%的“亮眼成绩”,实则依赖出售东莞旧厂房获得的1.72亿元一次性收益。
若剔除这笔收入,主营业务利润依然单薄。
下沉市场真的是救命稻草吗?郑耀南曾信心满满地表示:“县城的店基本都是盈利的。”
但现实远比理想骨感,在拼多多、抖音电商的冲击下,县域消费者同样追求“高性价比+线上便利”,而都市丽人的线下门店模式仍显笨重。
此外,品牌形象固化的问题并未解决,在90后、00后眼中,都市丽人仍是“妈妈辈的专属”,而新兴品牌通过社交媒体、KOL种草和极简设计,早已俘获年轻群体的青睐。
结语
都市丽人的困境,是传统零售品牌在新时代的集体焦虑。
它曾抓住每一次危机中的扩张机会,却未能洞察消费者需求的变迁,它享受了线下流量的红利,却错过了电商与社交媒体的转型浪潮。
它试图用“降本增效”止血,却难以掩盖创新乏力的软肋。
如今的都市丽人,像极了努力追赶时代的“追赶者”,既要在下沉市场与本土品牌贴身肉搏,又要在线上与新兴势力争夺流量。
想要极力摆脱“土味”标签,又缺乏颠覆性的产品与营销。
卖房换利润的短期操作,或许能让财报暂时“止血”,但若无法找到真正的增长引擎,这家曾经的“内衣大王”恐怕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。
市场从不相信情怀,只相信创新与价值,都市丽人留给所有传统品牌一个警示: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,终将被消费者遗忘。
相关内容推荐:
拓展阅读:
- 今日股市最热文章
-
- 吴小晖老婆是邓卓芮吗?邓卓芮的几段婚姻(40790人阅读)
- 安邦集团是邓家的吗?安邦保险幕后老板是谁?(31523人阅读)
- 镍矿概念龙头股有哪些?多家镍矿上市公司或将受益一览(14169人阅读)
- AI一键去除衣物网站 13免费裸体生成器和脱衣服AI工具(12048人阅读)
- 2020两会新政策20条是怎么回事?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(6168人阅读)
- 富国中证军工161024基金今天净值 161024基金历史净值分红(6127人阅读)
- 橡胶概念股上市公司有哪些? 橡胶龙头受益股票一览表(5581人阅读)
- 郎酒股票代码是多少?郎酒上市了吗?(图文)(5568人阅读)
- 孙宏斌背后的靠山是谁?(融创中国真正老板是谁)(5428人阅读)
- 软银集团股权结构持股比例是多少?(5016人阅读)